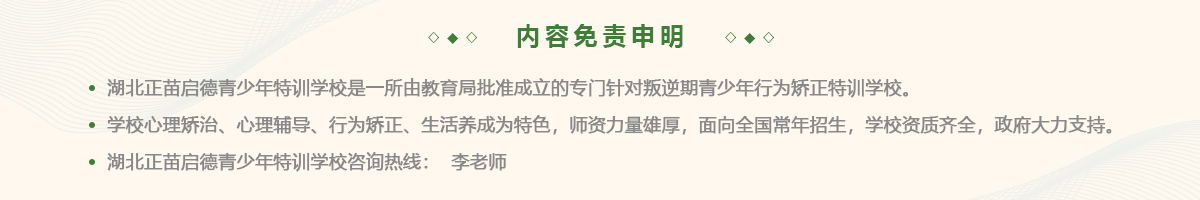儿时真正的苦难,儿时最痛苦的回忆,不是饥饿,而是读书。一个最大的梦魇就是背乘法口诀表。还没学过计数我就开始背这个鬼表,3+7又怎么回事呢,要理解3×7是什么意思更难理解。乘法口诀表原本乏味,如果不明白它的意思,背诵更是要命。越背越烦,越烦越烦。这位急躁的父亲开始用毒打折磨我,后来他又以挫败折磨自己。要不记得受了多少责备,也不记得挨了多少次毒打。
小时候家有一条狗,每次我出门回来,狗儿总摇晃着尾巴,蹦蹦跳跳,我有时会觉得要是狗子是对的,用不着看书写字,不必背乘法口诀。那时如果是在练习和吃屎之间作出选择,我肯定会立刻选择吃屎。
父母爱子不必怀疑,但父亲教导子女的作用是值得怀疑的。孩提时代,我和父亲的关系,不像父子而是仇敌。看起来我们之间除了被打和骂之外,没有任何其他的联系。只是关心儿子的学业成绩,一点也不在乎儿子的苦乐和悲喜,我没有感到一丝慈父之爱的温暖。爸爸去世多年后,我才能理解和宽容这位父亲,因为我教育儿子的方式,毫不留情地继承了父亲的“光荣传统”。年过半百了,我才真正认识到家教的问题。今日,我“声讨”自己的父亲,其实是自责。
我在向过去的自己道别。我与父亲完全相同——我们的生活非常普通;又与父亲截然不同——我可以接受平凡,并且可以享受平凡;父亲拒绝平凡,但更不能安分守己,因此,父亲从来都是面带愁容的,而我中年之后,总是微笑灿烂。通过自身的痛苦经历,我极端厌恶“望子成龙”的价值取向,它将温情的父母变成了冷酷无情的魔鬼,它让孩子的金发童年变成了一片灰暗。因为爸爸压力过大,整个小学阶段我都有些厌学,一直到初中一年级才喜欢看书,成绩也只能勉强过得去。三年级时,由于父亲越来越受到批评,他对我的学业越来越不感兴趣。您说怪不得,爸爸对我的学习越不上心,我对自己的学习反而越用心。以前是爸爸强迫我看书,慢慢变成了我主动去找书看。中学毕业时我各科发展比较均衡,偷偷看了一些“文革”前的小说,数学也不吃力。由不爱看书到想看书,我们乡下把这一情况叫做“玩醒了”,我真的像从傻瓜中惊醒一样。

中学生就是读书,远离父亲的“魔掌”,生活更自由,其实我比在家里更自律。虽然在中学时期是“文革”时期,但是邓小平已经出来主持工作,学校开始教文化课,高中三年一次都没斗过老师。语文、数学、物理、化学等课,老师们教的很认真,同学们也很用功。全班同学课内课余都偷看禁书,除革命导师、鲁迅、浩然等极少数人的著作外,一切人文社科书籍均遭禁。这类禁书被称为“黄书”,就连《唐诗三百首》也被禁止,更别提写爱情小说了,写妖魔鬼怪的《西游记》,写妖魔鬼怪的《西游记》,就是《唐诗三百首》,写得有血有肉的《红楼梦》。愈是禁书同学愈想「犯禁」,愈「黄书」同学愈想偷看,读书与亲吻一样,偷来的却格外香甜。偷看禁书紧张刺激,这就养成了我读书的习惯;下一位同学要看禁书,这又锻炼了我的精神高度集中的能力,同时也锻炼了我一目十行的阅读技能。那时候,没有了高考的压力,也没有了排名的紧张,学生们可以自由阅读。每个人都拿着家里的书到学校去传阅,一本书常常变成“猪油渣”,前后页全脱,书角全毛边,有的小说读完了还不知道书名。
我班有几个好读书的同学,几乎都在比武,谁声称自己读过了一本书,即使别人没看过,大家也会投上赞叹的目光。记得有一位同学叫胡利畅,他读书非常有学问,作文也写得很漂亮,有一次,他对我说,他读过郭沫若刚出版的《李白和杜甫》,我甚至没有听过这本书的书名,就觉得自己是浅薄之人。
中学毕业的时候,我读了不少中外小说,除了《金瓶梅》没有读过以外,现在通读的是所谓的“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”,《水浒传》的许多名句至今仍记忆犹新。由于高考的压力,现在的高中学生几乎不会通读名著,既不会读名著,也不会读名著。过度的压力、紧张的时间,会磨灭学生学习的兴趣,削弱青年求知的热情。因为阅读的门槛不高,阅读小说和人文作品是一种自然的行为,而对数学及其它科学知识的学习,与教师的课堂教学及课外辅导是分不开的,「先生领门」之后,「个人修经」才「修」。
同学们遇到一位什么样的老师,如同一位丈夫娶什么样的妻子,都是靠一个人的幸福和两个人的命运。吴先生毕业于华中师范,这是我现在供职的。有一次她见我爱瞎琢磨,常在课后还向她请教,便暗暗送我一本“文革”前的《初等代数》。这部数学书大约有四百多页,那时我如获至宝,立即从第一页学起,自学成材,就像一只猴子吃栗子一样,不知道该怎么下口,一开始进展很慢。遇到拦路虎时,不好意思常常打搅阮老师,害怕别人说阮老师是我的偏心,又无法和同学讨论。有一天早上下课后,阮老师问我学习到什么地方了,我一五一十地说出了自己的困难。看到我自学困难,她要求我每周向她报告一次困难情况。每个课后的练习题,不分难易我都做了一遍,做上记号难题第二天再做。每次课后,我都要在脑海中复述这一课的内容,归纳其重点、要点和难点,然后再进入新课时,先复习一下前两节课。一段较长的自学时间就掌握了一些诀窍,不仅进步越来越快,而且越学越觉得有味。揭秘就像攻破了一座城堡,我就像冲向敌人的城楼,挥舞着红旗的战士,心中充满了胜利的喜悦和豪情。
在学习了“初等代数”之后,阮老师送我一本《初等几何》。与解代数题相比,我更喜欢证几何。有时候一道难题要证明几页纸,一道难题证明出来后的成就感,没自学数学的朋友不能想象。一九七三年邓小平回归时,我们那儿也举行了数学竞赛,我在2000名选手中获得了第三名。假使当时像现在这样划分理科,毫无疑问,我将被划入理科班。同样,我的作文也写得很好,语文老师鲁绪卿和胡仲弼也经常给我戴上高帽子,可我的作文在班里却不是很好。
那时数学比现在高中数学的难度要小得多,竞争也不像现在那么激烈,也许我把自己对数学的兴趣,当成自己的数学天赋,恰如喜欢美颜的女生,把照片里的玉容当成自己的脸。三年的高中生活虽然是在“文革”中,但是我的求知欲望极强,遇到老师十分严肃,因此我的学业并未过分荒废。学业进步极快排在第二位,关键是养成喜欢阅读的习惯,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而且初步培养了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。
从自身经历来看,我一直认为兴趣并不是天生的,它是后天获得的结果。俗话说得好,把门出相,过去误认为是得自遗传,其实全是环境与教育的产物。小孩在什么样的家庭里,要遇到什么样的老师,他会喜欢什么学科或者讨厌什么学科,这有点像从前的女孩,嫁鸡随鸡,嫁狗跟狗,都要看自己是怎样的生活。